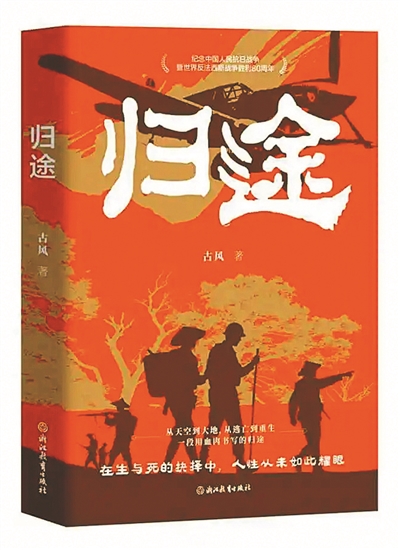
1996年为迎接香港回归,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计划把抗日战争期间香港沦陷的过程拍成电视剧,我应邀参与了策划和最初的剧本创作。正是从那时起,我便与“东江纵队”“香港抗战”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直到完成长篇小说《归途》,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回头看看,已过去近30年,一时间不免感慨万千。
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是我在研究香港抗战的资料时,发现“营救”这个词极为突出。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全面进攻香港。驻港英军自信十足地告知香港民众,香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日军占领。结果,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日军攻陷香港,时任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驻港英军仅仅抵抗了18天。此后,香港在日寇统治下进入3年零8个月的黑暗岁月。
香港沦陷后,大量英国军人成了战俘,被关押在不同的集中营里。此时香港还有近千位中国内地文化名人滞留。当年,许多作家、记者、导演、演员和反战人士为躲避战火逃亡至香港,如茅盾、邹韬奋、蔡楚生、胡蝶等。同时,支援香港的美国空军飞虎队成员也有多人因战机被击落而隐藏在香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此时的重要任务就是营救这些滞留人员到解放区或者国统区的安全地带。因此,描述香港抗战,“营救”是非常重要的题材。
我在近30年的创作过程中完成的电影剧本《克尔记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港九大队》,以及今年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归途》都与当年香港地区的“营救”有关。
《归途》主人公诺亚是被游击队和普通香港民众护送的一位美国大兵。他的归途,就是一段被无数善意托举的旅程。如果说诺亚的归途是线,那么其他人物就是线上的珍珠。
小说创作伊始,在我最早的大纲里,包括主人公诺亚、游击队队长梁波在内的那些英雄们都是近乎完美的角色。他们沉着、勇敢、技艺高超,有着深深的国仇家恨和强烈的英雄情感。他们满怀正义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参与到抗日战争中。但我偶然间读到一份美军飞行员日记,记录着他用口袋里几颗有些融化的太妃糖,作为和村里孩子破冰的礼物。这一行不起眼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我。我忽然想知道,那场宏大的战争背后,这些具体的、带着体温的瞬间,究竟是什么样的。
后来,当我看到那些战争中具体而微的细节时,我恍然悟到:一切宏大本质上都是由微小构成的,大道义往往出自小情节,大作为都是由小举动组成,英雄也大多由普通人构成。
在我读到的资料里,有战士们当年的日记,有对老战士们的采访,也有他们所写的回忆。这些材料让我看到更多历史细节:他们会记下腿伤溃烂时闻到的草药味,会清晰描述某个村民递过来一块红薯时手上的茧子,以及被陌生人救助后的笨拙感激。
所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修改了最初诺亚英勇无畏的形象,让他成为一个“馋嘴中尉”,让他怕黑,让他在山洞里因为疼痛和恐惧而发抖。我给游击队队长梁波设计的形象,是一个地方武装领导者。为了隐蔽身份,他戴着银戒指,使用象牙筷子,吸特制的烟斗……另外,我也想通过这些细节,让这个人物形象更有烟火气息。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写12岁的游击队队员陈树。他作为情报员和传令兵,连续几天都没有睡觉,也顾不上吃东西。在一次战斗中,他埋伏在山岗上,却沉沉地睡着了。直到战斗结束,战友们清点队伍时,才在阵地上找到他。这个情节是我在广州采访一位东江纵队老战士时听到的。我在写作这段的时候,一边笑,一边流泪。这是我们可爱的英雄,但他也还是弱小的孩子。
我觉得正是这些细节的存在,才让书中众多英雄人物所做的一切,显得那么珍贵。游击队队员们并非单纯的“拯救者”,他们本身也是需要被拯救的、活生生的人。战争逼着这些善良无辜的人们拿起了枪。如果不是日军的侵略,梁波会是造船厂的工程师、陈树也会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还有中药铺掌柜、大学毕业生、医学博士……无数普通人,都在一夜之间被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如果不赶走侵略者,他们就不会过上正常的生活。
写他们的时候,我常常要跟自己“想当然”的冲动博弈。比如梁波,我总想让他说点铿锵有力的台词,但后来我放弃了,让他大部分时间沉默,只用行动说话。看到诺亚的伤,他默默叫人去找药;面对怀孕的妻子,他把叮嘱咽回去,只投去一个眼神。这种“收着写”的方式反而让他更有力量。
最让我煎熬的,是写牺牲。书中人物的牺牲极为壮烈。但如何表达这种壮烈,让这些壮烈能够触动灵魂,是我需要思考的事。所以,这些段落我写得很慢,经常写几句就要停下来。最后,我依然选择了一种“克制”的写法。陈树的哥哥陈山跟着梁波和队友们去炸日军机场的油库时,被日军打死。失去好兄弟的梁波一行悲痛万分。他们逃出机场后,面对火光冲天的油库,默默无语。赶到现场的陈树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后,流着泪继续送信。
战争的残酷,不就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容分说的“失去”吗?当我写到战友们围坐在篝火边怀念牺牲的同志时,他们一开始都是沉默的,随后,有人低声唱起了队歌,缓慢而激昂,这种悲壮无需豪言壮语。
我不想用悲情去煽动什么,只想让这份沉默的力量,重重落在纸上,也落在读者心里。
书里的一些小物件,在我写作过程中,常常像是自己跳出来的。那双筷子,最初只是为了形成文化符号,后来越写越觉得,它承载的东西变多了。从江娇递出时的祝福,到诺亚笨拙地使用,再到几十年后艾米丽在箱底重新发现它。由这件最初的礼物上,我们看到一段被压缩的时间。梁波手上那杆刻满横道儿的烟杆,既是战绩簿,也是一个人的过往。同样,那些太妃糖、戒指、手表、糍粑等物件,它们在故事里生长,最后成为比台词更有力的语言。
写到尾声,我忽然明白了。我写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记忆如何活着”的故事。那些在抗战烽火中被打捞起来的人性光辉,并没有熄灭。它们通过一双筷子、一个故事、一个名字,悄无声息地流淌下来,流到了今天。
写《归途》,对我而言是一次灵魂的沐浴,也是一次人性的触碰。我希望读者能透过这些文字,看到战争的伤痕,并触摸到那些伤痕之下,普通人身上的坚韧与温情。那或许就是我们在绝境中,能真正依赖的“光”。



